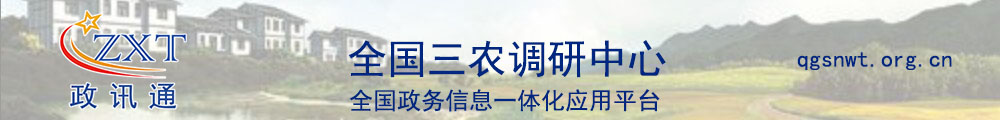奥赛博物馆
巴黎奥赛博物馆大展厅内
巴黎塞纳河左岸河边上有座很宏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这里原来是专门为1937年巴黎的国际博览会建造的火车站,叫%26ldquo;奥赛火车站%26rdquo;(the Orsay),原建筑设计师是维克多.拉洛克斯(Victor Laloux)。当时的功能有点像现在的轻轨捷运系统,是专门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送到展览中心的交通枢纽。博览会结束之后,这个火车站还继续使用,直到1939年的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后来就废弃不用了。到底巴黎火车站够多了,北面有北站、东站,东南面有里昂站( Gare de Lyon),火车站够用,何况在市中心那么高级的住宅区里再保存个火车站,影响周边环境。这个车站废弃之后,好长时间都没有用,建筑倒是好得不得了,屋顶上全是雕塑装饰,门前有%26ldquo;新艺术%26rdquo;风格(Art Nouveau )的装饰玻璃大棚顶,一组黑色青铜的世界各个洲的女子雕饰屹立大门一边,个个都是丰乳袒臂,性感得很,这样的建筑空置不用,实在很浪费。
世界上最早举办世界博览会的国家是英国,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为此还特别建筑了%26ldquo;水晶宫%26rdquo;这样庞大的温室型建筑,出尽了风头。法国人自然不肯让约翰牛专美,因此在19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一个接一个的开博览会,规模一个比一个大,在塞纳河两岸,可以看到好几个历届世界博览会留下的建筑物,体积庞大,设计精美,艺术高超,是去巴黎很值得参观的项目。
巴黎塞纳河左岸河边上这座很宏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就是奥赛博物馆
奥赛站这个建筑物长期没有人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里因为够大,就做了战俘中心,基本就是个监狱。战俘遣返之后,建筑物又关闭起来,之后给一个剧院当排练场,战后巴黎百业萧条,城市里到处都是新古典主义的精品建筑,但是都处于很荒废的状态,还有谁考虑这个旧火车站呢?
巴黎战后的文艺复兴其实开始于乔治.蓬皮度总统时期。蓬皮度发起大规模的巴黎文化复兴运动,投入巨额资金修缮旧建筑,改作各种文化用途,其中包括了把奥赛火车站改造成为一个艺术博物馆。
法国政府是法国最大的艺术收藏单位,这点与美国大相径庭,美国的艺术珍品,一多半都是私人收藏的,法国从波旁王朝开始,政府就收购艺术品,有时候还会特别约艺术家为政府创作,这个传统持续到今日,政府继续不断收藏当代艺术品,政府收藏品数量特别庞大。19世纪以前的艺术品,在罗浮宫展示,罗浮宫体量大,加上贝聿铭又设计了新的地下贯穿结构和几个新的建筑庭院,足以展示大部分历史收藏,之后又建造了庞大的、高科技派风格的蓬皮度文化中心,专门收藏展示现代艺术品,而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叶的艺术品就有点尴尬,因为放在罗浮宫太新,放蓬皮度文化中心又太旧,蓬皮度总统就提出改造奥赛火车站为艺术博物馆的设想,目的就是放这一段的艺术品。因此,1986年奥赛博物馆开幕,专门展示法国政府收藏的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叶的艺术品,现在已经成为观看这个时期法国艺术作品的最佳去处了。法国人有了钱就想着将传统的好东西修复整理,发扬光大,比我们那些一有钱就只想着拆的人高明太多了。
奥赛博物馆屋顶上安放着法国历史上著名文化人的雕像
蓬皮度发起大规模的巴黎文化复兴运动,投入巨资修缮旧建筑,改作各种文化用途,其中包括了把奥赛火车站改造成为一个艺术博物馆。
奥赛车站的改造工程是在1983年到1986年间进行的,建筑师是R.加东(R.Gardon)、可巴(P.Colbac)、菲利普(J. Philippon)等人,室内设计是奥连提(Gae Aulenti),聪明的利用车站改造,美轮美奂,是我见过全世界最好的博物馆建筑之一。这个博物馆在90年代又再改造过一次,设计师的名字刻在入口的一块石碑上。说起建筑师的名字刻在建筑上,这也是巴黎的一个好传统。这些著名的大建筑自不必说了,我在登上蒙马特高地的途中,也注意到楼梯旁的老住宅上也刻有建筑师的名字。这除了表明对建筑师创意和劳动的尊重以外,也赋予了建筑师一份社会责任%26mdash;%26mdash;真名实姓刻在上面,你还敢弄个豆腐渣工程出来吗?
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叶这个时期简直不得了,因为是古典艺术逐步衰退,现代艺术开始开始萌芽的时期,刻画人民真实生活的写实主义兴起,出现了库尔贝、米勒这些非常具有革命性的新艺术家,又继而产生了印象派、后印象派这些初期的现代艺术流派,在奥赛看艺术品,整天不出来也就仅仅跑马观花而已,要看好,起码得去好多次。这个时期作品的浓度、精度,在世界绝对第一。
一组世界各洲女子的黑色青铜雕像屹立在大门一边
我记得国内曾经翻译出版的唯一的一本现代艺术史-美国H.阿纳森的《西方现代艺术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出版)中一开头就谈到库尔贝( Gustave Courbet),这本书是国内的一个建筑家邹德侬翻译的,国内的艺术理论界也实在丢人,这么多年就没有一个人能再写本超过阿纳森的作品来,即便讲翻译水平,邹先生的依然还是最好的,我就不知道这些年培养了那么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世界艺术史专家在干些什么。这本书开始就讨论现代艺术的开始,提出有几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说是开始于库尔贝的作品。不过后面又把新古典主义的大维特、盎格尔当作开端讨论,说法多了,读者看了还是不清楚。
我在去奥赛之前是没有见过库尔贝的原作的,所有的作品都是在画册上看到的,感觉题材平民化,的确不同,但是色彩灰暗,大约是那个时代法国底层民众的心态的写照。去了奥赛,看到原作,的确很震惊,因为它们都巨大无比,实在难以想象。1855年画的《画家工作室》(或者翻译为%26ldquo;画室%26rdquo;),副题叫%26ldquo;我作为一个艺术家和一个人的七年生活记录%26rdquo;,3.59米高,5.98米宽,鸿篇巨制,要退好远才看得到全貌;另一张作品《奥南斯的葬礼》(a Burial at Ornans),宽度接近7米,这样巨大的作品,除了大维特受拿破仑委托画的拿破仑加冕之外,世所少见。
我们在%26ldquo;文化大革命%26rdquo;期间是画过这样大的画的,那都是毛泽东的肖像,谈不上艺术,就是给民众去崇拜用的。而大维特的画,是拿破仑拿来纪念自己丰功伟绩用的,也谈不上多么高的艺术价值,而库尔贝则是为自己的信念画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丰富的馆藏雕塑
平心而论,库尔贝在西方画家中,算是最得国内宣传机构长期善待一位。1950、60年代,一个%26ldquo;形式主义%26rdquo;就足够整得你去劳改,戴上%26ldquo;右派%26rdquo;帽子,永世不得翻身。此风刮自苏联,其实很荒诞:艺术不讲形式讲什么?真是有点莫名其妙,中国不但忠实地学习苏联这套教条,还加以极端化发展,除了写实,一律行不通。因此,在中国少数一点点介绍西方艺术的出版物中,西方那些%26ldquo;形式主义%26rdquo;的流派,一律入另册,什么印象派,野兽派,简直是腐烂资本主义的象征,画画怎么能够凭印象的呢?画画要面对火热的生活,面对工农兵;什么野兽派,一定是叫野兽来画画了,不是说美国动物园让大象用尾巴画画吗,这就叫%26ldquo;野兽派%26rdquo;,最集中显示出西方意识形态的极端腐朽。超现实主义,超越现实,扭曲我们美好的时代,简直是反动派。%26ldquo;达达主义%26rdquo;,你想%26ldquo;达%26rdquo;什么?用心叵测。而库尔贝画农民,画平民,反映人民生活真实面貌,因此是%26ldquo;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26rdquo;,与专画农民的米勒一起被介绍。60年代初期,我看过国内出版的一本介绍西方油画的小册子,其中以库尔贝、米勒、杜米艾、夏尔丹为法国现实主义的最高代表,我对库尔贝的印象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
库尔贝的作品的确很坦率的表现了自己的情感,自己的信念,他绘画的方式也很粗犷、草率,如果看惯了学院派那种精雕细作的人物画,看他的画是觉得有些伤风败俗的。他的主题往往是社会的下层,小人物的故事,并且画面永远有种非常浓郁的黑色基调,我看用黑色用得那么有明确的目的、用得那么淋漓尽致的画家,除了他就很少见了。
奥赛博物馆藏画
奥赛博物馆最精彩的藏品自然是19世界下半叶的绘画,晚期浪漫主义、社会写实主义,特别是印象派和后印象派、巴比松画派这类,在全世界博物馆收藏之中是登峰造极的。设计收藏也是这个时期的最精致,比如%26ldquo;新艺术风格%26rdquo;(Art Nouveau)的收藏,我看世界上无馆能出其右的。
一个火车站可以改成那么好的一个博物馆,我们现在城市改造,不少城市废了不少旧的工业、交通建筑,一股脑儿拆了。其实学习巴黎人,改造它们,赋予它们新的内涵,恐怕比推倒重建更加精彩。看看奥赛,一定有体会的。
馆中小憩
摘自《巴黎手记》
2009年11月26日,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