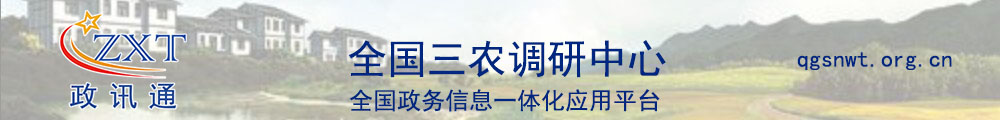诗歌为什么重新引起大众注意?
【归来者-洪烛与古筝诗歌谈话录】节选[1]
一、归来者说:重新做一个诗人
洪烛:在郑州开的那个会,说起归来者这样一个现象。我当时的感觉是什么?就属于韩作荣谈起的那样。写诗的人就像抽烟的人似的,他戒掉了之后,有可能再吸,再吸后有的就反而抽的更猛了。诗歌是一种瘾。人啊,就是说真正热爱诗歌的人,他是没法忘掉诗歌这种东西的。我也就这个话题,当时谈到好多诗人的离开和归来,就%26ldquo;俗%26rdquo;的方面来打个比喻,就像一个回锅肉似的,它回锅之后,他真正的创作才成熟起来。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都是那种青春期的写作。
古筝:青春期的写作,按照现在的说法来说,谁都可以写,青春本来就是一首诗。
洪烛:是啊,那谁都能写。青春期的写作一般都有很多原始的感觉,比较感性。但他真正的中断一段时期的诗歌,或者说离开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到诗歌,基本上他就进入了第二个创作阶段,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阶段。
古筝:那是他在经过反省之后,就是经历过对前面一个阶段的反思和脱离中成熟的。
洪烛:这个阶段是什么?就像小别胜新婚似的,我说的是跟诗歌之间。就是说你离开诗歌这段时间之后,然后又重新回到诗歌。你离开写诗,实际上后来更加热爱诗歌。你之所以离开后还能再回到它身边。
古筝:就是说它对你还有一定的吸引力,它还能够让你回来,就很不容易了。
洪烛:是很不容易。这种选择是你自己选择的,应该是一种选择了。
古筝: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你还是朦胧的,是不知不觉的走进去的,或者是被外力推进去的。
洪烛:一开始喜欢诗,好多人都是一种兴趣,或者是原始的一种感觉,当时就觉得写诗好。但他后来离开后又真正回到诗歌,一定是经过理性的判断了。觉得自己是离不开诗歌,才重新回到诗歌的。这确实是他生命中不可忽缺的一部分,他才回到诗歌。也有很多人离开诗歌后,他有可能一辈子不写诗了,诗歌对他来说只是生命过程中的某个东西,也许是他年轻时候有这种愿望和需要,然而一旦真正进入现实社会后,梦想和现实很遥远,这个梦破灭之后,他有可能再也不做这个梦了。
古筝:也确实有不少人没有回来,过去和我一起写诗的朋友,现在有不少在做官,或者继续在商场拼搏,还有的在那个年代就出国寻求发展,再也没有回来。
洪烛:这样的人非常多。我举个例子,就像徐舒他们,他可能就觉得诗歌和他的生活很遥远。其实,诗歌就属于信则有,不信就无的。你相信它,它就存在,就有它的力量,而且就对你的生活产生很多的作用。但如果你不信它,它就什么都不是。
古筝:对,你相信它,它就存在,才有存在的价值,不然它确实就什么都不是了。
洪烛:所以我当时谈到归来者的现象,那些归来者吧。当时,我怎么讲了?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吧,进入新世纪以来后,和80年代在文化气候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为谁都知道80年代是一个诗歌的春天,当然90年代可能是一个冬季了,整个诗歌都进入冬天,好多诗人都进入冬眠的季节,都停止了写作,或者离开,都改行作别的去了。
古筝:是92年之后。
洪烛:对,92年后特别明显。就是说是季候性。当时我就想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大批的归来者呢?因为全国各地我接触的好多诗人,都是80年代写诗,90年代改行,然后现在又重新写诗。我的感觉,我就想,这几年大家都知道诗歌很繁荣,是因为诗歌的繁荣吸引了很多的诗人回归呢?还是有大批回归者增加了诗歌的繁荣?
我当时分析了两种原因兼而有之。有些回归者他确实是这几年诗歌繁荣的中坚力量,因为他们有过80年代的那个经验吧,而且归来者还确实保持着80年代的那种激情,对诗歌确实充满激情的,还有很多的经验。就是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就是对这批归来者,我觉得是诗坛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力量。就像王小妮80年代写诗,她最近这些写的诗歌的总的名字,诗集的名字就叫《重新做一个诗人》。归来者他一般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在重新做一个诗人。你重新做一个诗人,就比一开始就立志做一个诗人,实际上我觉得更成熟了。
古筝:从我自己的现在和过去的写作中,对此我也深有体会,因为我也是一个归来者。重新做一个诗人和立志做一个诗人,在起步上就不同,而且上的台阶也不同了。
洪烛:对,起步就不同了。而且重新做一个诗人是自己的选择了。你确实知道是为诗歌而活着,或者说诗歌是特别适合自己的,他这种选择是非常坚定的。而一开始的选择不一样,一开始他的选择随时有可能放弃。
古筝:前面的选择多半是受到环境的影响,或者他人的影响等因素,是在朦胧中走进诗歌的,自己是不自觉的,后一种选择则是经过放弃的考验和理性的分析。
洪烛:就是说80年代很多人写诗,就像一种初恋的感觉,实际上他不懂爱情,他不懂诗歌是什么,他在那个时候写诗了。
古筝:那就是你所说的青春期写作,有的是激情,诗人不缺乏激情。
洪烛:他有激情,他也容易失恋,也容易离开诗歌,放弃诗歌。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归来,他都是在重新做一个诗人,他基本把诗歌做一种婚姻来选择了。我就是说,一开始立志做诗人,等到重新做一个诗人,就是初恋和婚姻的区别。婚姻它肯定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对吧?和那种初恋不一样。初恋它可能很多都是一种瞬间的、暂时的,在这点上,我后来分析归来者它为什么是诗坛的中坚力量呢?因为他经过了过去,经历了那种放弃,他重新选择了,他肯定是非常有意识的,不是那种无意识的选择了。在这点上,从那个对歌的态度上是这样,我当时觉得归来者心理变化过程就是这样的。
第二个就是他们的技法上。我认为诗人一定要经历春夏秋冬。你因为80年代是诗歌的春天吧,谁都知道80年代是诗歌的春天。但他经历过夏天、秋天、冬天之后,四季的轮回之后,又回到第二个春天,他又重新开花了。实际上,他经历过那种落叶的时候,萧条的时候,什么都经历过了。在这样的春天中,他又开花了,开出的花肯定比第一个春天更艳丽。
古筝:他有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对此,我深有体会。
洪烛:而且他还有一种沧桑感。因为他经历过那种四季的轮回了。
古筝:所以他后来的作品就比较厚重,而且还有生命的体悟。
洪烛:就是他们自己的作品和80年代相比,就像你的作品,你的《虚构的房子》和80年代的诗歌相比,我真的感觉有天壤之别,那种感觉。因为80年代的诗歌,你还是比较感性的,非常优美。好像我们中间还见过一次,你那时候对徐志摩好像是特别崇拜。
古筝:那时候我觉得他的音乐感、抒情和优美,对我的影响特别大。80年代的朦胧诗追求意象和半透明,现在看来也是在一种文字表象上做文章,但在当时有它积极一面和先进性。到了现在,回过头来再写诗,那就是追求一种力量美,把生命中的领悟,融会贯通到字里行间。虽然也通过一些意象来达到传递,但它里面隐含了较深的内涵,它不单纯是表象的,肤浅的一种词语的堆积,一种那样的东西。因为这些和你后来的生活积累有很大的关系,你对一些事物的理解和剖析,和一种感悟都渗透到你的作品中,它们不是刻意的,而是水到渠成,自然的流泻出来。就是说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后,你在各种经历的磨砺和挫折中成熟起来,同时带动你的作品成熟起来。而且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剩下来是很多时间你在思考和反省,确实是这样的。虽然时间的流逝,使你失去了青春,却在返回时收获了一个成熟的秋天,再像返老还童一样,你突然进入你诗歌的第二春。所以他的诗歌就变得厚重起来。不会像以前那样仅仅停留在诗歌的表面,完全追求唯美,一种直白的,情感单线条的东西,以前他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我在网络上读到不少80后,90后的作品。80后的还好些,尤其是90后,应该说还刚刚接触诗歌,他跟我们80年代写东西的感觉是一样的,它完全是属于青春期的写作,他不知道该怎样写出属于自己个性化的东西,追随流派,潮流怎么写我就怎么写。当然他写出的东西也是诗歌,但我只能说他是在模仿和写一些诗歌皮毛的东西,或者说展现的内容是文字的表面化。
洪烛:或者说就是比较原始的。这就是还停留在初恋的阶段,他不懂得爱情的时候。他写诗了,他不懂得诗歌是什么,但他爱上了诗歌。
但我现在看你的诗歌,我倒是觉得,你观念上的转变给我的印象比较深。那个时候,实际上你是把徐志摩当成你诗歌教父的那种感觉。
古筝:确实,我崇拜徐志摩,这种崇拜也是和那时候的年龄是契合的。
洪烛:他是你诗歌中一个偶像。但是,我觉得你现在的诗歌中有好多是徐志摩所不具备的东西,这是我自己的感觉,也是我对你诗歌的感觉。就拿你《虚构的房子》中好多近期的作品来说,实际上在某种程度后你又超越了你自己。当然,你超越了你自己,就是超越了徐志摩。因为你以前的自己,基本上一直都是在徐志摩的照耀之下。
古筝:我有时候在想,我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喜欢徐志摩,甚至整本的背诵他的诗歌,最后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一种艺术的美对人有黑洞一般的吸引力,它把我吸进它的世界里,而无法自拔。就像我后来也喜欢和接受席慕蓉,就拿席慕蓉来说,很多人都说她的作品比较浅,她的作品看上去比较容易读懂。但我和他们的想法和理解有差异。我就是觉得席慕蓉的东西容易和我产生共鸣,能够给我感动。你能够在她简单的线条中,读到一些生活和情感的体悟,这些感觉,特别是女性的诗歌比较细腻,就像蚕丝一样缠绕着你,特别容易使你产生怜惜和共鸣,以及对一些无法挽回的时光的怅愁,心灵在读诗歌的过程中得到或者进行了一种碰撞。徐志摩的诗歌则给我另一种享受,是不一样的感觉。那么说,就现在的诗歌该怎么写?特别是经历去年网络诗坛发生的那么多起事件,我们该如何看待现行的诗歌流派和走向,自己又该如何写?诗歌的出路该在哪里寻求发展和创新?不过我是从来不跟风,随便外面各种流派闹的怎样纷纷扬扬,我最多只是一个怀有好奇心的看众。
我也从来不反对各种流派,包括口语。如果说到口语,我觉得有些作品还是写的很不错的,不仅亲切还比较新颖。但是我不喜欢把生活中的说话简单的复制成诗歌,那么这种口语就变成了一种口水,实在是没有兴趣去阅读。我觉得就算是口语吧,也要有一个提炼和艺术化加工的过程,在艺术上下点功夫,也应该经过沉淀,再展示的呈现。因为任何艺术不管以任何形式的呈现是要给人以享受,或者思考和思想的光芒,在这点上,不管是审美还是审丑。
当然我不是提倡刻意的去雕琢,但我想玉经过雕琢也是一种美,清水出芙蓉也是一种自然美。其实不管你怎么做,你拿出来的东西,要具有可读的价值,或者说阅读快感。自然美不是你早上起床不洗脸就出门,那是对自己和别人的不尊重。那么,现在回过头来说,我看到网络上那些泛滥的口语。啊,那是我日常怎么说话我就怎么写,甚至把恶俗的骂人话,儿童不宜的话都在夹杂其中,以为这就是先锋和革命的。其实这就走到另一个极端了,任何事情一旦走到极端必将面临死亡,这就是后来人们开始对口语反胃的原因。诗歌该向什么方向发展,语言该寻找怎样的出路?如何把口语从口水中解救出来?我想这些都是很多诗人正在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再度返回诗歌的我来说,我不会去盲目的跟风,像80年代那样懵懂的写作。我很清楚的给自己的诗歌做了一个定位,那就是界定在传统和先锋之间,传承的同时又力求突破。
三、预测:诗歌主流将在传统和先锋之间
洪烛:今后的诗歌会从口语的极端,又开始新的流向。
古筝:你是指传统的回归吧?
洪烛:就是在传统和先锋之间的诗歌。我觉得诗歌就像一个钟摆似的,永远在先锋和传统之间摆来摆去。
古筝:其中还有一种挣扎。
洪烛:对。这是一种生命力。它永远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它如果不是像赵丽华他们这样走到这个极端,就没法焕发那种力量。它到了这个极端了,它肯定是要回荡的。但我觉得真正的好诗,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就在这个极端向另外一个极端摆动的时候,一种过程中。
古筝:在这个过程或者最后无法支撑的时候出现的。
洪烛:所以,我自己预言,06年是诗歌向种庸俗化写作的极端撞出的一个钟声,但钟声之后,它要回归和摆动了,摆动向2007年,是属于另外一个极端。向传统摆动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会出现一批好的诗人和好的作品。就是有一批诗人他也在反思,如果把诗歌全部推倒这种极端好不好?诗歌使得很多诗人有负面的影响。明明想的,本来像伊沙和赵丽华他们,都是希望通过自己偏激点的举措来吸引别人的眼球,让别人关注诗歌,用意都是好的。
古筝:还有舒非苏是吧?
洪烛:舒非苏。本来他们的用意可能是好的。但由于选择的行为太极端,所以反而使诗歌蒙难了。但很多诗人会在这点上进行反思,实际上在反思的时候,就会出现一批相对来说比较折中点的诗人,折中点的诗歌作品。我自己觉得真正的从艺术价值上来说,好诗是相对有它的折中性的,就是说在传统和先锋之间。传统的优点它能汲取,它两方面的缺点都能排除。
古筝:它在传统的基础上还可能需要一种探索的意识。
洪烛:所以我自己感觉,可能在2007年的时候,很多诗人会变得清醒一些,是吧?很多诗歌也会相对来说,我个人感觉,他会出现一些经典的作品。经典的作品,它就属于并不是那种偏激的,并不是在诗歌史上能够留下一个痕迹,它改变了一个诗歌的河流,使诗歌的河流改道了,它并不是,而是在一种正常的河道上掀起了一道波浪。
古筝:这是比较冷静和客观的分析。
洪烛:所以,我倒是个人觉得,客观的评价去年的好多事件,偏激点的诗歌事件。它也许都是在为2007年在做一个准备。所以在2007年的时候,诗歌它也许会像从真正的恶梦中醒来似的。它醒来之后,它可能会真正的出现一大批,我认为好的诗人和好的作品,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古筝:我觉得,这中间可能有一段恢复期。
洪烛:恢复期。对。你可能觉得2007年还没有从振荡中走出来。
古筝:我觉得,上半年还应该是一个恢复期。
洪烛:我们在北京的好多诗人,就拿前段时间林童写的《网络时代的长诗现象探测》来举例,包括我自己的%26ldquo;西域%26rdquo;,还有好多。他当时觉得这些长诗的出现,基本上也就是一种反思产生的,诗人就要开始增强写作的难度,就是说诗歌它有一种写作的难度。
古筝:那海子当初不也是在写长诗,他的那些近乎史诗的诗歌,不也是要追求这种效果吗?但是一直都没有引起重视,你觉得在今后会引起重视?其实,我个人的体会是,特别长的诗歌和特别的短的诗歌最难写。
洪烛: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对啊。但我觉得长诗,可能下面会非常重视诗歌的经典,为什么那么多诗人开始写长诗,就是开始渴望经典。诗人希望自己的作品并不像梨花诗那样,成为口水诗那样,不是一次性消费的那种,他希望能够有长远的价值的。
古筝:就是那种能够让你反复看,你每次读都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体会,越看越觉得有嚼头,这样的诗不仅耐读,而且才能留下来。
洪烛:所以我感觉到,通过梨花体和口水诗之后,梨花体和口水诗是有它的好处是吧,使得很多诗人意识到,诗歌不能永远这样走下去。它的意义就在这个,所以你不能说它没有意义。通过这个,使得诗人开始觉悟诗歌不能这样走,而想到诗歌应该怎么走,它的意义还促使诗人冷静下来。
古筝:纵观一代又一代的诗人走过的道路,包括朦胧诗、新生代、口语、下半身等。现在回过头来看,从传统到先锋之间是一条真正的道路。以前那么多的诗人过去了,他们每个人留下了什么?大家都可以审视一下,什么东西最后才能留下来。比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就流传下来了,还包括北岛的《回答》,就是说必须要有经典之作,诗人和诗歌都需要沉淀。我觉得,现在是诗人他太浮躁了,他在这种浮躁的环境中沉不下来。他想的就是怎样去炒作,快速成名,期望有一条成功的捷径。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下,他更多的时间和功夫是消耗在诗歌之外了,他也无法写出经典作品来。在心态上,就是说诗人的心态出问题了。他受到外界的诱惑和影响,学那些演艺圈的明星大肆炒作自己,就是说现在的诗人也在干这样的事情,而且它考虑一个市场化的问题,诗人已经和纯洁不能划等号了。
洪烛:但是,我为什么并不否定伊沙和赵丽华他们呢?一方面不单是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啊。我倒是觉得,诗界也需要这样的清道夫。我自己个人觉得,他们属于诗歌的清道夫,或者说他们是探地雷的,他们是在雷区中,就是说他们的那种破坏性,也是他们的革命性,他们是一种破坏的力量。但是,他们是为后面的人铺路,或者清道的。
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是说他们永远在诗歌发展到一个极端,他们是在用另一种极端来反击以前的那种极端。我举个例子,诗歌就像在钟摆边摇摆。在五、六十年代,大跃进时代,流行的就是那种民歌体的,或者像郭小川的那种,任何人都能听懂的,为政治宣传的,政治口号的那种诗歌。后来为什么朦胧诗会为何出现呢?因为诗歌永远都在看懂和看不懂之间摇摆。50年代的这种诗歌说白了,它就像一杯白开水,白开水似的诗歌。后来吧,朦胧诗就像鸡尾酒似的,并且还尽量把它调的就像化学试验似的,然后那种又走向朦胧诗的极端。
古筝:朦胧诗走到极端的一些具体的表现,就是最后要煞费苦心的去猜谜,和只能看不能读了。
洪烛:然后就出现第三代诗歌。第三代诗歌是反击朦胧诗的,当时就是要让北岛%26ldquo;pass%26rdquo;,就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就是朦胧诗那种看不懂的又回到第三代,第三代就属于那种反对高贵的,一种平民化的,就觉得诗歌就该平民化的,然后第三代又走向极端。第三代走向极端后,诗歌就开始进入真空,又没法发展了,没有力量了,它在这个极端没法摆动了。这时候出现了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它是为了反击第三代诗歌的。
古筝:感觉他比朦胧诗更晦涩。
洪烛:对,它更看不懂了。就因为第三代太让人看得懂了,然后就出现了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一旦出现之后,诗歌反而萧条了,读者更少了。
古筝:因为晦涩,大家都看不懂,所以它的阅读圈子越来越小了。
洪烛:都是纯阳春白雪的,都是那个小圈子,实际上当时的现象是,写诗的人比读诗的多。
古筝:然后就萧条了,好多诗人就是在那个时候离开诗歌的。
洪烛:然后90年代就萧条了。诗歌进入知识分子写作后,那种书斋似的,就和现实生活无关的,一种玄想似的,诗人的那种玄想似的,是吧?这时候,大家都说诗歌看不懂了。所以,我个人说,这个时候伊沙的出现,是有他的革命性的,就通过%26ldquo;饿死诗人%26rdquo;的口语,口语诗。我们不要觉得口语不好,口语最初出现的时候,它是为反击知识分子写作的,它有它的革命性的。所以,好多东西要这样看,它好多破坏性的东西是有革命性的。
古筝:但它最后控制不住了,就让人反感了。
洪烛:对,它失控了。我说伊沙他们通过口语化来反击知识分子写作的那种,然后,诗歌就从知识分子书斋似的写作进入口语化的那种极端了。口语化持续的时间,一直持续到赵丽华的梨花体,一直持续到这个时候。但我现在的判断,下面的诗歌又会摆脱口语化。
古筝:会不会一下又走入晦涩呢?
洪烛:我个人倒是觉得不会。在这点上我觉得,因为它已经经历了两重到三重的摇摆。
古筝:从朦胧诗到第三代,第三代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到口语化。
洪烛:从以前大跃进的诗歌到朦胧诗,然后朦胧诗到第三代,第三代到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到口语化的写作。现在的诗歌,它再摆动,它也不会到看不懂了。诗人通过诗歌的几次发展,几次摆动,诗人开始在反思。
古筝:不管怎么考虑,诗歌还是要向经典发展,诗人同时不能丢失广大的读者,也不愿意丢失广大的读者,所以就不能写大家都看不懂的东西,那样读者会必然流失。
洪烛:从我自己要求自己,要汲取两方面的优点,摒弃两方面的缺点,摒弃它口水化的那一面,但汲取它口语化的一些优点。
古筝:对,口语化确实有它的优点,它在朗诵上和语言的犀利上都直抵人心。
洪烛:口语化确实是有它的优点,我们不能否定它的优点。
古筝:当然不能否定,也无法否定。
洪烛:不能因为口语诗后来怎么了,我们就把它全盘否定了。因为我觉得过去的诗歌老是在全盘否定中。为什么老是这样。我觉得现在的诗人应该有意识的,就是对过去的两个极端都不该给它全盘否定。我觉得,在下面的诗歌就该汲取两方面的优点,一方面,就像口语诗写作那样离现实生活贴近,贴近日常生活。
古筝:你分析的很透彻。
洪烛:这两方面的优点是可以汲取的,写作适当的口语确实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这方面的优点可以汲取,但摒弃它那点庸俗的东西。因为口语化,实际上它也容易走向庸俗,把庸俗的东西丢弃,但同时又汲取知识分子的那一块,知识分子他们有很多精神上的东西,还是需要汲取的。
就像我评价你的诗,给你写的诗评里也提到这点,就是把它看成哪怕一尊座神似的,非常敬仰,就是说诗歌有一种高贵,诗人和诗歌就应该保持这种高贵,这个我觉得是不该否定的。
古筝:我觉得这两方面有个融合的问题,好东西都汲取了,这样好的东西都同时放在里面,搞不好会有不伦不类的感觉,这就是最要命的。
洪烛:但这个也是最考验诗人的。就你一个诗人,必须博采两家之长,而且实际上是很难的。一般可能会这样,可能伊沙写不出知识分子写作的东西,但是可能是王家新、西川也写不出伊沙的东西,口语化的。
古筝:我是觉得,它可能和诗人个人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
洪烛:和诗人的个性有关系吧。但是,我倒是觉得,诗人下面会有意识的调整自己,就是一种在汲取,在改良自己。因为通过以前几次诗歌的震动,我就觉得,革命的一条路,容易使诗歌走向毁灭。下面的诗歌不会是革命了,它开始走改良的道路了,我觉得下面的就是那种改良道路的诗歌了。
古筝:可能应该会是一种缓和地、温和的,对吧?温和的那种。
洪烛:对,温和派的。我就是说,诗歌的温和派会出现,温和派的实力会逐渐强大。
七、洪烛说:做一个诗歌的赤脚大仙
古筝:有时候长时间的离开也会形成了一种断裂。
洪烛:就是一个人和过去的自我一刀两断,一刀两断不是为了断裂,而是为了重逢,还是为了重塑新的自我。虽然说那时候也有诗人要谋生,但没有因此离开诗歌,主要是内因的作用吧,不仅仅是外力。
古筝:摆脱外力的作用,他不会是因为现在的离开是为了回归,他不会有这样的想法的。如果说回归,那是因为再一次受到诗歌的诱惑、吸引和刺激。对我这次的回来,我是这样认识的,其他人是怎样的,我不是很清楚。
洪烛:离开是为了归来,这是一种规律。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枯木逢春了。有的诗人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断裂自己,选择了自杀,另外一种像海子,戈麦,这种是消极的。后来我分析了,一个诗人啊,他为选择了自杀?是因为他诗歌的创作穷途末路了。如果一个诗人处在上升阶段,不断超越自己,他是不会去自杀的,也是自信的。但一个诗人的写作成为一种惯性,无法超越和摆脱自己,无法写出更好的东西了,所以消极的选择自杀。
我认为断裂有两种:一种积极的,另一种消极的。我和你都是属于前一种,那时候我们可能是在终止了我们的诗歌生命,但我们可以随时复活,因为我们的生命仍然存在,生活仍在进行。
古筝: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海子的现象体现了诗人精神世界的脆弱,而且这种脆弱是那样的不堪一击。相反,诗歌却是那样的坚强,无论你离开,抛弃,或者自杀,它依然还是活着。当你选择回来了,它还是在那里等你,你无法不热爱这样一种永恒的事物。
洪烛:围绕你这个断裂,我觉得我们的离开,它他是一个藕断丝连的,丝还连着,就像春风吹又生,一旦气候适合,马上就能焕然一新,开花结果,甚至比一开始更有激情。海子则是真正彻底意义上的断裂。
古筝:而且还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般80年代写诗歌的人,现在基本都已经进入中年阶段,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诗歌是属于年轻人的,只有年轻人才能写出激情澎湃的诗歌,因为他有的是热血和激情。但是我觉得这批回归者的归来,他们并不缺乏激情,还更多了成熟和沧桑和经验,这些感悟体会在诗歌中更有成熟的韵味和耐咀嚼的价值,就像你说的,他们的回归是在繁荣了诗歌的再度春天,而且这次的回归,激发出的更大的热情。
洪烛:他不但有热情,而且还高于早期的热情。就像我前面谈到的,这种重逢是小别胜新婚的感觉,它比新婚更热烈。他后来对好多感觉有更深刻的认识,对诗歌也是,你离开后还能回来,你将更加坚定的热爱。
离开有两种:一种是放弃,放弃者自然有归队的可能。另外一种像海子那种是属于消极的离开。在这点上我后来分析,当一个诗人的创作一直处在一个平面的时候,或者是真的走不动了的时候,怎么办?这个一个命题。很多诗人走不动了,他就觉得自己江郎才尽了,因此心灰意冷。但是真正的诗人还是应该面向生活,哪怕中断,离开一段时间的诗歌创作也可以。他面向生活,然后你具体读书,或者充电,也许你回来后,你比不离开,一直在写更好。因为我分析过,如果我前面的8年一直在继续写诗,就不会出现我现在的这种个人化的诗歌风格。为什么这几年我的诗歌质量有所提高?这些都因为这8年离开的积累。如果每年都在写,每年都在消耗能量,那么我的诗歌就不会那么集中,我这几年把8年积累的感觉全部写出来了。
古筝:诗歌确实是需要在生活中沉淀后,然后厚积薄发,才能爆发出潜在的能量和熊熊的火焰。我在想像海子这样的诗人,他作为一个完全为心灵写纯粹的诗歌,对生活太理想化了,其他的都忽略不存在,那么外面的大环境的改变,必将会对他造成致命的打击。作为一个诗人,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诗人,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那么谋生对于他来说也该和普通人同样重要的。你也该以生活为根基,融入生活的精彩和杂乱中,这种生活酸甜苦辣的感受才能让你的诗歌和生命更丰富多彩。
洪烛:这绝对是对的。
古筝:你老是每天面壁苦思冥想,写那些不断重复别人或者重复自己的东西,不仅苦闷还确实很无聊。
洪烛:你没有那种生活体验,你就没有生活那种后续的能量。后来我就觉得你8年没有写作的生活,对你后来的诗歌是有意义的。
古筝:还有我后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2000后网络的迅猛发展,进入网络后,那时候又开始接触到诗歌,那时候的感觉真的是倍感亲切。虽然我没有第一时间内恢复诗歌创作,但一直在关注着诗坛的动向,怀有深深的好奇,这么些年后,还有那么多热爱诗歌的人活跃在网络中。后来,我开始着手写小说和散文,小说和散文的写作对我后来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帮助,帮助我在语言上放松自己,做到更流畅和随意。这是因为小说追求质朴的语言,越接近生活的语言越亲近大众,其实在我的散文中也融入了许多诗话的语言,虽然这些不是分行的诗歌了,但有些东西你无法彻底抛弃的干干净净。由于诗歌的语言和小说语言,还有思维方式的截然不同,小说要求的语言完全生活话,朴素化,个性化,在写小说一段时间后,它在语言上就给我早先模式的诗歌语言解压,让诗歌语言从而变得放松,甚至有脱胎换骨,可以有飞起来的感觉。后来我的诗歌中,也有部分作品中揉入少量的口语,并把小说的场景写法运用到诗歌中。我要说的是,一个诗人不要单纯的局限和死在诗歌中,可以尝试也写点其他的文本,当你再返回时就会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神奇的看到自己的新面孔。
洪烛:这点上,我们的感觉是不约而同的。当时我为什么写散文呢?就是对自己的诗歌比较失望,一写就是那种雕琢的东西。我们都是80年代写诗,一直到92年,当时是什么感觉?一写文字就在下意识雕琢自己。弄得我连写信都不会写了,你写什么都要用写诗的方式,诗歌的语言,好像得了语言障碍症。
你想什么时候都穿着诗歌的靴子,写什么东西都下意识的要求语言优美。后来写散文,就是为了摆脱这种雕琢的弊端。因为散文相对来说就比较放松些,有的就和说话一样。就是为了恢复被诗歌压抑很久被束缚的技能。有那么一个时期,感觉自己都不会正常说话了,那样久了真的很难受。什么都要讲究用意境、形象的东西来表达。我确实为了摆脱语言上沉重的靴子,想要做一个赤脚大仙,不穿靴子,体会那种不穿靴子的感觉。
我当时的印象特别深,写一封信都要雕琢语言,但久了之后真的很难受。后来写散文就是为了磨砺语言,就想用一些粗糙的语言。因为以前的语言都太细腻了,就像被砂纸打磨过一样,非常精细,所以就想粗糙点,就是不雕琢,我在想看看如果不雕琢会怎样?
古筝:这样是感受我们是共同的。我前面说了小说和散文对我诗歌的语言帮助很大,就和散文对你的诗歌语言的解放是一样的。我现在的诗歌语言就显得自然了许多,不那么紧绷。
洪烛:后来我的诗歌也因此写的反而轻松了。虽然有些散文化。正因为我后来写了8年的散文,就把散文的优势也用在诗歌里面了。
古筝:是啊,我很赞成你这个观点。
洪烛:我现在倒是觉得各种文本是可以杂交的。比如诗歌太像诗歌了,也不是好诗;散文太像散文,不是好散文。上次我在访谈里说过:我写散文也要求自己把诗歌用在散文里,使自己写的散文不像散文。当时我这8年的散文还是有一定的特色,至少说我的和散文家的散文不一样。因为我当时觉得诗人的散文肯定要比散文家的好。
古筝:诗人的散文要优美一点。
洪烛:我后来把好多诗歌的优点用在散文里,再后来写诗歌,又把好多散文的优点汲取在诗歌创作中。所以,我现在的诗歌,它不像以前一直作为诗人写诗。因为长期作为一个诗人来写诗,你会下意识的雕琢,会过于在乎语言。那时候你就进入最后的穷途末路。我觉得诗歌,使得你就觉得诗歌就是语言。我通过8年的不写诗歌,我改变了观念,语言只是诗歌的形式而已,还是得靠内容。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