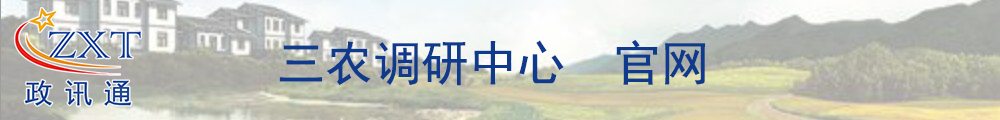《中国站起来》序
吴洪森让我相信在这个时代的世界上还有挚友,而他的朋友魔罗则让我相信在这个时代的世界上还有神交。因为,我至今还只和摩罗见过一面。
最早听说摩罗的名字,以及阅读摩罗的作品,都是拜洪森兄所赐。摩罗对于我,意味着剧烈的冲击和绵延的记忆:摩罗的思想是喷涌的熔岩,摩罗的文字是犀利的斧钺。一切模糊和常识都被他的思想烧炼,一起虚伪和结论都被他的斧钺责问。每一次读完摩罗,我都必须俯首捡拾起自己的知识碎片,重新整理缀合。我相信,这就是摩罗的力量;而如此强大的力量,在今天是绝不多见的。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私言。请看:
摩罗的文章是20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 %26mdash;%26mdash;余杰
几年来,每逢读到摩罗的热血文字,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挚友感到光荣和骄傲,可是又担忧,担忧他因此蒙受更大磨难,担忧他老是面对这些令人义愤填膺、血脉贲张的问题,损害健康。 %26mdash;%26mdash;吴洪森
来自底层的摩罗,常识问题既是他的出发点也是归宿。平等、自由、正义、公正和良知,是他承诺的必须维护的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尺度。%26mdash;%26mdash;%26mdash;%26mdash;孟繁华
余杰、吴洪森、孟繁华都是我内心非常敬重的人,他们和摩罗的交往,以及对摩罗的理解,都是我无法比拟的。但是,我之所以相信和认同他们对摩罗的判断,绝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名字和品行,而是,他们说出的正是我心灵深 处的感受。 摩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26ldquo;一个世纪过去了,历史没有满足我们的期待,而是赏给我们更多的丑剧和闹剧;民族没有回答我们的呼唤,而是加给我们更多的奴役与凌辱。我们这些将醒未醒的奴隶,只有带着最大的哀痛,彳亍于时间的黄昏,无望地临风而歌。%26rdquo;这段话,至今还在我的读书笔记里,未敢或忘。 但是,摩罗终究是一个临风亢立的歌者,即便哀痛,甚或无望,他都只会笔直地站立着,直面所有的奴役与凌辱,直击所有的丑剧和闹剧,大声呼唤出他的期待和希望,穿透漫长的时间走廊。这是令人油然生出敬意的伟大史诗般的悲壮努力。 《中国站起来》正是努力的结果。摩罗是一位作家、诗人、学者,然而他更是一位知耻的勇者。摩罗的评论者注意到,在他的文字中,%26ldquo;耻辱%26rdquo;象茫茫夜空中的闪电一样,刺破浓浓的黑暗,挑开我们被遮蔽的良知。
摩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26ldquo;一个世纪过去了,历史没有满足我们的期待,而是赏给我们更多的丑剧和闹剧;民族没有回答我们的呼唤,而是加给我们更多的奴役与凌辱。我们这些将醒未醒的奴隶,只有带着最大的哀痛,彳亍于时间的黄昏,无望地临风而歌。%26rdquo;这段话,至今还在我的读书笔记里,未敢或忘。
但是,摩罗终究是一个临风亢立的歌者,即便哀痛,甚或无望,他都只会笔直地站立着,直面所有的奴役与凌辱,直击所有的丑剧和闹剧,大声呼唤出他的期待和希望,穿透漫长的时间走廊。这是令人油然生出敬意的伟大史诗般的悲壮努力。
《中国站起来》正是努力的结果。摩罗是一位作家、诗人、学者,然而他更是一位知耻的勇者。摩罗的评论者注意到,在他的文字中,%26ldquo;耻辱%26rdquo;象茫茫夜空中的闪电一样,刺破浓浓的黑暗,挑开我们被遮蔽的良知。正如《中国站起来》的副标题所在昭示的那样,摩罗关注的是%26ldquo;我们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26rdquo;。他的歌、他的哭,他的喜、他的哀,所关乎的都不仅是他个人。尽管我们知道,摩罗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摩罗年长我五岁,而我将他视作兄长,却绝不仅仅因为序齿的关系。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人生轨迹几乎全不相同。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精神自有契合。摩罗在%26ldquo;后记%26rdquo;里说:%26ldquo;我这本书本来就是写给70后、80后、90后一代人看的%26rdquo;。摩罗和我都是60后的一代,我们又凭着什么可以写给后来者看呢?《中国站起来》是摩罗的答案。我的答案是,或许我们还曾经在理想主义的岁月里浸润过,虽然在记忆中,理想难免堕入虚妄,但是,理想对于我们,依然是一个美丽而高尚的字眼。正因为此,我们除了微笑和冷漠之外,还会歌,也还会哭。
我之所以愿意、敢于给摩罗的《中国站起来》写序,并不是因为我赞成摩罗的所有主张。摩罗不需要世俗的客套和伪饰。对于摩罗新书里的不少见解,我都持有不一样,甚至很不同的看法。只不过,我坚持认为,我们不能没有刺破迷雾、击透寂寥的歌哭者。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向摩罗这样的歌哭者致敬,是我无尚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