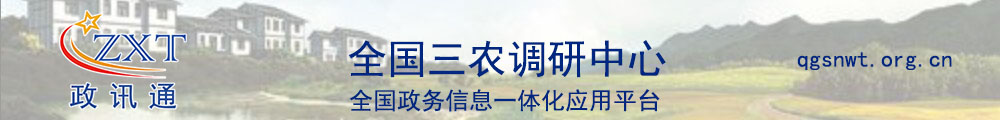旧宫殿 4 祝勇
拾肆
建文元年(公元一三九九年)七月五日,朱棣智擒了驻防北平的张 和谢贵,夺占了九门,誓师起兵,开始了一场长达三年的“靖难之役”。
像所有的战争一样,三年中充满了离奇和曲折,故事层出不穷,诡谲的细节许多年后还在戏文里抑或说书人的口中复现——关于攻与守、进与退,关于计策与阴谋、忠诚与背叛,关于在血刃里茁壮生长的野心,关于你死我活。发生过厮杀的地方都变成巨大的坟场,无数双圆睁的眼睛被大地所掩埋,战士的视线永远被黄土遮挡,永远无法看到战争的结局;如果仔细谛听,可以从风声中辨识出死者的呼号,以始终如一的韵律,在坟场上空回旋不已。只有朱棣的梦境,在纷乱的硝烟中日渐清晰。他骑马穿过冰河,目光已经穿透丛林,看到钟山暮色中的宫阙灯火,看到一张苍白而年轻的面孔自幽黯处浮现。他离他的侄儿越来越近,他饥渴的剑,即将刺入那个属于江南的小生脖颈。目的地越来越近,令他兴奋。风卷走了血的腥味,朱棣不会回头去看山岗上成片的死尸。他举剑,刺入冰冷的空气。他确信远方的朱允炆能够感受这一刺。他分明感到剑尖在他颈骨上遭遇的阻力,伤口鲜血迸溅,利刃恶毒地欢叫着,在他的喉结上打了个滑,就“扑”地一声从颈后穿出。他几乎可以看见朱允炆颈后绽放的血红的花朵。每一滴腾飞的血珠都圆润饱满,油光绽亮。拔剑的时候,他感到剑已被对方的脖子吸住,于是迅疾地抽出,同时听见了哀恸的声音自空气中颤动而来,不是发自口中,而是发自脖子上的血洞。
与朱棣的想象不同的是,年轻的朱允炆在故事结束的地方为自己预备了一把火。他回避了朱棣的剑。刚刚听说金川门之变的消息,无处可逃的朱允炆就已经决定蹈火自焚了。这一点恐怕连他自己也未曾料想。他从未注意过由“文”和“火”两个字组成的“炆”字对命运的暗示。宫阙里闪跳的火苗中透露着随时可至的凶险,在更多时候,这种暗示消隐在灯红酒绿的宴乐里。终于,宫殿毁了,火灭了,只剩下一具面目难辨的尸体。
建文四年(公元一四0二年)六月,朱棣挥师顺利进入南京,正式登基,建元“永乐”。朱允炆死后的南京陷入空前的狂欢中。
【宫殿】
拾伍
在中国的古迹中,没有一处像故宫这样拥有显赫的位置,如同一条无用的旧闻,却仍占据着头版头条,又像它所代表的皇权时代,迟迟不肯退休。
对于许多从没进去过的人来说,故宫是他们想象中的天堂。在很长的时间中,只有很少数身份高贵的人才能走进它,才能目睹它的华丽与神圣。绝大多数普通人,只有蹲在皇城外的筒子河边,通过高于树梢的城堞,揣测它的细节。宫墙保守着宫廷的秘密。即使站在合适的角度上,他们也只能看到故宫上面的白云。
我看见一片白云停在午门的正上方。红色城墙以蓝天为背景,显得格外夺目。手里攥着一张门票,我迟迟不往里走。我望着午门发呆,想象着很多年前一介平民对于故宫的想象。
拾陆
对一座皇宫的诞生进行描绘无疑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能对营造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没有一个人能够见证建造它的所有细节。每个细节都有来头,都有另外的细节藏在背后,这些背后的细节会合谋新的细节,新的细节又彼此勾连,派生出更新的细节。当一座座雄伟的宫殿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已经无法计算,它究竟跨越了多少个细节,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我们站在它的面前,只能看到它正面的局部,而永远不可能看到它的背面——包括空间的背面,和时间的背面。
我们看到高贵的金砖开始覆盖粗糙的土地,辗碎了旺盛的杂草——左右磨砖对缝的“海墁”砖地都用澄浆新样砖以“五扒皮”的做法,縐砖精墁;汉白玉须弥座层层浮现,铁钎在阶石上飞舞,巨龙沉重肉感;我们看到红墙一道道地竖起,在斑驳黯淡之前如同火焰一样明亮耀眼。它把所有的声嚣都聚拢起来,包括人的呐喊与机械的喘息,昼夜不停地喧响,仿佛对一场战争的重演。在没有梦境的地方,天堂却难以置信地浮现。
我们看不到的部分却是:那些在宫殿里飞来飞去的奏折,与奏折相关的阴谋、千里之外的战争,功臣的封赏、死人的头颅,转瞬倾覆的王朝、惊恐万状的宫娥、密如雨林的箭矢……时间隐匿在空间背后,不被人察觉地干预着营造宫殿的进程。如果我们站在时间的维度上做逆向推算,我们就会发现,每一截宫墙的出现,都可能与先前的某一事件有关。许多看似无关紧要的机遇最终决定了成千上万的砖石金玉最终将在哪个位置上出现。大片大片的金砖覆盖了原来的战场,土壤中的骨殖鲜美如肥料,梁柱斗拱在它们上面无所顾忌地疯长。
没人说得清宫殿是在哪一天建成的。几百年中,它们一直是建建拆拆,拆拆建建,像变幻的海市蜃楼,一阵风就能吹乱它坚硬的线条。遥远朝代的构件,在这个宫殿中不曾间断地连接,时间像偶尔清锐的磬音,或者含冰的凉露,显形,又融化。每一个皇帝都认为他是始建者。他要尽可能地毁灭前朝的细节,让自己成为万物之始。
当然,这不可能。
拾柒
朱棣说:朕要迁都北平。
皇帝的决定意味着,在战争停止之后,苦役又开始像瘟疫一样蔓延。它跨越省界,使二十三万人纳入它的控制。寻找珍贵木材的行动在四川、两湖、两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大面积展开,在宫殿最初的轮廓远未形成之前,就已经有许多人死在山野间,他们的生命如同被伐下的巨木,在悲惨的断裂声中戛然而止。他们被未来的柱檩压死,他们腹腔里喷涌的五色的肚肠为宫殿漆上最初的彩绘。但他们仿佛从未存在过,华丽的殿堂在北方的土地上渐渐显形的时候,他们却在南方的湿泥里慢慢腐烂。穿梭的公文中的没有一个字与他们有关,因为他们无关紧要。
被热汗渍红脸额的男人们注视着炉膛里迅猛的火焰,窑里正在烧制宫殿里的金砖。他们无法想象它们在蓝天下大面积辅展的壮观景象,他们只关注金砖出窑时的成色。那不仅与这些艺人几辈子的名声有关,更与他们的性命有关。我曾在烧砖地——苏州探访金砖的制作工艺,了解到此砖需用太湖湖底多年沉积的故土,经过二十六道工序精细加工而成。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说,制成此砖的时间长达二年,仅烧砖的时间就达一百三十天。砖制成后还要在桐油中浸泡一百天。苏州的水土与工艺,四海之内首屈一指,即使在烧成后需要漫长的运输,也在所不惜。作为一系列复杂而严谨的工序的结果,金砖有着无比坚硬的质地和打磨规整的外形,有“千年不毁”之说。我用手轻轻敲击,在听到金属之声的同时,看到金砖露出刀刃般锋利的棱角。据说,修造北京宫殿,总共用掉八千万块砖。八千万分之一,卷帙浩繁的古卷里一个无足轻重的零散词语,依旧经历着漫长的酝酿、选择、推敲过程,以使它与其他词语的连接平滑无隙,组合成庄严的圣典。
如果我们能够取得一个更大的视角,我们会看到大明帝国版图上一幅奇异的图景:无以数计的车马载着沉重的木石,从不同方向汇聚到北京。衣衫褴褛的队伍在山河间行进。征夫们的肉体骨骼被负重挤压得变了形,他们的报酬在道路的尽头等待着他们,那报酬是——或许能够得以苟活。车流在版图上不断掀起的巨大烟尘十几年未曾消失,征夫们脚踩着混合在泥土草梗中的死亡骨架,奔向那正在兴起的明日之城。一些细小的被太阳晒暖的尘粒不时掉落到头顶,仿佛来自太阳的告诫,让他们不可在代表着冥所的道路上停留太久。多年以后,当所有远方的珍木巨石聚合成一片广阔的宫殿,成为天下最荣耀的场所,那些高贵的礼仪和血腥的阴谋在其中展开,古道上飞扬的尘埃才渐渐落定,覆盖曾经深刻的辄迹。道路归于静寂,日寒草短,月苦霜白,时间抹平了一切痕迹,仿佛宫殿和王国从天而降,无辜的死者从不存在,连尸体都踪迹全无。
拾捌
工具。除人之外,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运输和装载的工具。台基、台阶、梁柱、御道,宏伟的宫殿,使得许多构件尺度都无比庞大,它们的重量足以使肉身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我们无法想象山岩被人们搬动,即使是群体作业,每一只手臂上蕴藏的力量也终将被消解得无形。如果不借助工具,石块木料就永远无法在都城汇聚,除非它们真如史籍中所粉饰的,“一夕自行若干步,不假人力。”(吕毖:《明朝小史》卷四,《神木山》)是工具,将山野间的原始材料与雄伟壮丽的宫殿建立起联系,如同苦力们脖颈上的锁链,在生与死间建立起联系。
我们永远无法看见搬运的过程,也难以想象工具的庞大——显然,工具的尺度规模,是被木石材料的尺寸所规定的,我们只知道巨大的梁枋柱檩、阶石栏杆,无一出自京城,而产于遥远的异乡,这些物体在如此遥远的空间中的神秘转移,使我们的想象鞭长莫及。无论我们面对哪一座宏伟的建筑,无论是埃及的古金字塔,还是英国的巨石阵,我们都会产生同样的困惑。当然,翻阅记载可以使我们知道一些事物,比如三大殿前后每块重达二百多吨的御道石,是从四百里外的河北曲阳运来的,聪明的工匠想出旱船滑冰的办法,沿途打井,利用冬季低寒的温度,从井中取水,泼路成冰,用旱船装载巨石,拉拽前行。四百里的路程,快马一日可达,而运送这只块巨石,动用两万多名苦力,排成一里长的队伍,每日也只能移动五里。据说后来创造了一种十六轮的大车,但每日也只能达到运送六里半这个极限数字。即使这样的记载,也只是凤毛麟角。我们很难对物体的连续位移进行破译。巨大而玄奥的工具消失在宫殿身后,使时间出现缺口,宫殿的呈现更加神秘。
拾玖
也许应该对专制制度心存感激——如果我们想目睹宏伟的宫殿。专制至少具备这样的好处:为了实现统治者的梦想,真的可以做到倾国倾城。宏伟的建筑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专制时代的产物,也只有最残酷和血腥的专制,才能将破碎的版图拼接在一起,并且使得地区利益乃至个体生命都显得微不足道。只有皇帝的利益才是最高的利益,皇帝的任何一句言辞都是法律,一句顶一万句,皇帝的意图,在任何时候都可能置换成全体人民的意图。皇帝的野心需要用战争来兑现,人民便拿兵器来说话;皇帝需要威武的宫殿,人民便投入一场没有尽头的苦役,以便皇帝能够站在豪华奢侈的宫殿之上,享受权威,发号施令。
西方人把万里长城视为人类创造史上的奇迹,他们往往忽略了这座宏伟工程所蕴含的暴力色彩。他们不能想象长城的建造过程,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曾拥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他们的帝国东征南讨,可能占据地中海沿岸的广阔疆域,可能建造巨大的斗兽场和古城堡,但即使如此,帝国的版图依旧与大秦帝国无法匹敌。即使中国人,也只能借助想象和有限的记载,接近阿房宫不见边际的形体,想象秦始皇君临其上的无比威严。营建长城的可能仅仅出于一种闪念,这种想法的产生或许与一个农夫用篱笆圈起自家的院子没有区别,只不过秦始皇的篱笆要把一个国家圈起来而已。后人对这一行为的赞颂,与其称道他的想象力,不如称道他手中的权力。他能获得一切,首先是因为他能剥夺一切。
贰拾
明成祖朱棣决定迁都北平,无疑是一项大胆的决策。本来在南京,他什么都有,包括现成的宫殿。那里是他父亲的纪念碑,他曾在那里度过自己的童年时光。现在,他要在北平再来一座。愿望十分简单,描述它甚至用不了十个字,只因它出自皇帝之口,人们知道它不是胡言乱语,不是痴人说梦,是永远无法违抗的圣旨。
这意味着南京的宫殿中每一个精致的细节都可能被复制到北平,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宫殿的复制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代价问题并不是坐在龙位上的皇帝需要考虑的,他只要结果。没有什么比结果更重要。
元朝的大内已被全部拆除,为的是破坏元朝的王气。朱棣对它们十分熟悉,作燕王的时候,他的王府就设在元代的大内里。现在,他要那些像山一样起伏的金黄的琉璃瓦,像白云一样交错排列的台基栏杆,那些金光闪烁刺人眼目的蟠龙柱、藻井、御座、屏风,统统在原来的位置上复现,而且规模更加宏大。消失的部分不可能重现,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我们只有顺着时间的指引,想象一座宫殿的诞生。
蒯祥是过程的参与者。这位年轻的匠人第一次走进毁弃的元代皇城时,他就已经看到一座座新宫殿在天际线下辅排开来。他在想象中完成着它们的轮廓。多年以后他才发现,他当初的想象已经精确到毫厘之内。蒯祥那时只有二十多岁,却已经得到主持宫城营建的蔡信、杨青的重用;那时他还没有想到在蔡、杨死后,自己会成为工程主要设计者和指挥者,直至成为工部左侍郎。但站在千疮百孔的大内庭院里,他感到血往上涌,像朱棣面对战场时那样,他预感到这项壮美而残酷的计划将奠定他的基业。
作出壮美然而残酷的决定是帝王的癖好。迁都决定的作出,除去他曾作过燕王这类个纯个人好恶方面的原因,和所谓边疆形势所迫之外,还需归因于他需要一个更加辉煌的皇宫来与他无边的权力相对应。在南京,朱棣的宫殿在规模形制上超越朱元璋已无可能,而荒芜空疏的北平,刚好给他提供了实现野心的空间。他不计代价地获取了权力,势必不计代价地享用和展示权力。
宫殿,就是权力的视觉化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