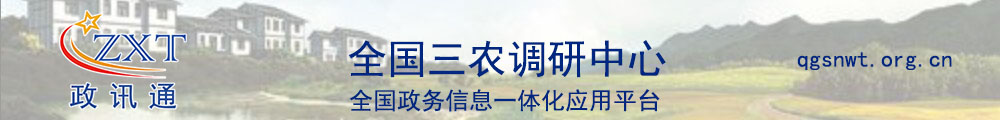反阅读 7 祝勇
三
然而,革命并没有履行它对胃的许诺。萧长春用丰收验证了合作化路线的正确,但他对胃部前景的乐观估计并没有持续多久,连年的饥馑便接踵而至。(1960年春,中国出现第二次大办食堂高潮的时候,粮食危机已经显现。如果此时不再办公共食堂,取消粮食供给制,将粮食直接分配到户,允许社员耕种自留地,粮食虽然少点,但社员自己可以干稀搭配,饭菜搭配,多种蔬菜,粮食的不足,可以渡过难关。但是,把5亿多农民重新捆到公共食堂,在口粮标准一减再减、蔬菜副食又几乎没有的情况下,结果可想而知。1960年,粮荒已经开始危及社员的生存。——据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第19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961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即《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信阳地委的这个报告,夸大了敌情,混淆了敌我矛盾,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作法。中央批示肯定了信阳地委的这个报告,并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这一批示助长了整风整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24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961年3月底,新乡地委在给河南省委的报告中说,尽管整风整社运动的开展和生活方面采取了紧急措施,但全地区2月份每日平均死亡人数仍有420名,但比1月份每日平均562名下降了25%26bull; 2%。全地区尚有9000万斤的食粮缺口。尤为严重的是全地区48%的食堂没有菜吃,31%26bull; 8%的食堂只能吃到3月底。河南滑县从1960年11月至1961年1月13日,全县共死亡2872人。该县白道口公社一个大队,1961年1月13日一天的时间死亡9人。——据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第204——20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请参见本书第 页注1。)《绿化树》(以及新时期的大量作品)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胃部的生理活动没有因社会秩序的改变而有丝毫改变。迈斯纳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
革命未能取得革命领导人及其思想家所期待的结果,这在现代社会主义革命中并非罕见。社会大革命总是由对未来完美社会秩序的乌托邦憧憬所推动,但革命一旦结束,这种辉煌的乌托邦憧憬也就随之消失,这已是一般的历史常识。这一现象并不简单地只是掌权的革命者背叛了他们对崭新的更美好社会的理想和憧憬(虽然这也是屡见不鲜的现象),而是革命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形势迫使变成了统治者的革命家们同现实和旧传统妥协。革命胜利后乌托邦的社会目标成为形式化的象征,人们还利用它来使新形式的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压迫合理化……
在革命取得成功之后,社会采取的发展方向常常与人们最初的预言大相径庭,那些曾对革命起过巨大推动作用的乌托邦社会憧憬也渐渐淡薄乃至泯灭……如果对未来的乌托邦憧憬在革命胜利后还存在的话,它们也只能是被歪曲的,变了形的。它们不是作为建立新机构的基础,而是变成了公式化的政治口号,用来证实新的社会秩序的合理性,而这种新的社会秩序和它原来的概念相去甚远。确实,革命的悲剧就在于乌托邦式的理想演化成哲学的陈词滥调而不再是激励社会行动的活生生的动力。
([美] 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Marxism,Maoism and Utopianism:Eight Essays),第187、18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艾萨克%26bull; 多伊彻斯在评价英国清教徒和法国雅各宾派革命时说:“革命的不现实性不要起源于^造**群众的过高希望和这种革命的资产阶级局限之间的矛盾。”(Isaac Deutscher,The Unrinished Revolution:Russia 1917-1967,p.27,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而迈斯纳更深切地认为:“革命乌托邦理想和客观历史局限之间的矛盾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表现得尤为尖锐。”([美] 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Marxism,Maoism and Utopianism:Eight Essays),第18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为了避免失掉信誉,革命必须及时进行一次语义调整,将革命的内涵,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领域。革命的出发点——生存的现实主义,也就转换成它的终极目标——精神的理想主义。身体在完成了它的使命之后,此时已被视同粪土,不登革命的大雅之堂。据雅典的苏格拉底先生论证,肉体在“本质”上就是尘埃的意思。遭到革命的拒绝,“苦行”、“禁欲”,忍受身体苦难,则成为革命者的必修课,而对于饥饿的态度,则成为判断真假革命者的试金石。在本书下一章将要讨论的《红岩》一书中,刘思扬有这样一段话:“在绝食斗争中,想到饿,甚至感觉到饿,都是可耻的事!当然,饥饿并不因此而不存在。可是,我要和它斗争,我要战胜它!这样一来,饥饿的感觉仿佛怕我似的,忽然偷偷地消失了。”(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242、24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OOO年第3版)正常的生理需求,此时已被赋予了严肃的道德语义。马尔库塞说过:“社会主义世界同时是一个道德的和美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含有唯心主义因素。”(H%26bull; 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见《工业社会和新左派》,第81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人或许可以不屈服于饥饿,但怎样才能如刘思扬所说“不感觉到饥饿”,确有唯心主义倾向了。这表明革命意识形态将苦行唯美化的政治唯美主义追求。在经过大力倡导之后,苦行美学逐渐深入人心。其中,方志敏的叙述堪称经典范本:“为了阶级和民族的解放……我毫不稀罕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栗和菜根!不稀罕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猪栏狗巢似的住所!”(方志敏:《清贫》,见《方志敏文集》,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饥饿在这里已经受到革命的彻底排斥。将身体苦难合理化,使革命越来越与宗教殊途同归。“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成为对革命的最高礼赞。
“饥者歌其食”。崇拜食物可以说是身体的本能。物质的丰裕本来是穷人投奔革命的最初动机,现在,它又被当视为道德上的邪恶与堕落而予以否定。最有趣的是对食物的态度——在《红岩》的同一段落中,对食物有一段这样的描写:
几十个饭桶整齐地摆在院坝正中。里面盛着的,不是污黄发臭的霉米饭,变成了热气腾腾的白米饭。一大桶油浸浸的回锅肉,分成了几十份,搁在每一个饭桶上。
“老刘,你看见了吗?”余新江厌恶地扫视着正在分肉的特务,对刘思扬说:“真是无耻的诱惑!”(同上书,第243页)
饥饿是特务们最大的帮凶,它几乎可以成功地攻克每一个坚强的身体。但是在革命者这里,它遇到了最强大的阻力,他们向饥饿发出的挑战,表现出一种圣徒式的勇敢。它奠定了革命者的饥饿美学。它令我联想到卡夫卡的小说《饥饿艺术家》。作为作家本人最为珍重的几篇小说之一,这篇小说描写了一个把忍受饥饿当作艺术的人。每当他表演饥饿的时候,公众都以不信任的目光窥探他是否偷食。这使他深受羞辱——饥饿是他的信仰,绝食是他的良心渴求。“他的艺术的荣誉感禁止他吃东西。”(卡夫卡:《饥饿艺术家》,见《卡夫卡文集》,第1卷,第22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最后,他用生命捍卫的自身的艺术尊严。刘思扬们的绝食当然不是表演,而是他们的斗争手段,就像战士用枪战斗一样。刘思扬与饥饿艺术家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饥饿的超越。
但是,对勇敢者的颂歌,同时也成了对食物的咒语。作为革命者意志的对立面,珍馐美味一律成为堕落的同义语。在革命作品中,只有地富反坏右,才大吃大喝(在革命文本中,对阶级敌人的妖魔化经常通过对其饮食的渲染来完成,比如我童年时代熟悉的电影《红色娘子军》、《闪闪的红星》中对南霸天、胡汉三的刻划中,都曾以食物为道具,突出他们的腐朽生活。这一手法在“文革”中被发挥到极致,在红卫兵的大字报中充满了对食物的诅咒,以此来认定“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属性”,比如,一篇题为《赫鲁少奇在昆明》的大字报写道:“刘鬼夫妇讲究吃喝,排场之大封建帝王为之咋舌。他俩口子每天需吃三只肥鸡,并且喝汤不吃肉。他们的鸡汤用锅炖的不行,要吃用汽锅的蒸馏汤。他们每餐要喝香槟酒,而每瓶只喝两杯就不要了,下顿饭又得换新一瓶。他们的早点离不开燕窝、银耳、莲子、鸽蛋、鹿筋等等。他们的菜既要有地方特点,又要营养丰富,如田鸡、石硼、熊掌、鹿筋等。”“为了这对狗夫妇吃得好,昆明的黑帮们从全省搜罗了各种各样的名产佳肴供其享用并找来昆明最好的厨师。可是刘鬼仍不满意,还特意从北京带了一个师傅来,专为他做菜。什么宣威火腿,滇池金钱鱼,什么过桥米线,北京烤鸭……真是五花八门,数不胜数。饭后,外国带来的水果削了皮塞到嘴里‘帮助消化’。每天黄昏到花园里,伸腿舒腰,养身修道。”见红三团《战地黄花》总队“专揪刘、邓、陶”分队:《赫鲁少奇在昆明》,已收入谭放、赵无眠编:《文革大字报精选》,第483页,香港明镜出版社,1996年版。而一篇名为《彭真的腐朽生活罪行》的大字报中,则专有《生活腐化、讲究吃喝》一节,文中说:“彭贼家五口人吃饭,每月开支伙食费达三百余元,平均每天七十元,比一般工人生活水平高七八倍。每天吃的是富强粉、小站米,一年四季新鲜蔬菜不断,连冬天也是吃鲜黄瓜、扁豆等等,鸡鸭鱼要吃活的,肉蛋要吃新鲜的。”“彭贼的生活不仅平时如此高标准,就是在三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也毫不减色。在困难时期,中央规定国家干部按人供应粮、油、副食品等,可是彭贼哪管党纪国法,旧市委、旧市人委、公安局等单位的黑帮,积极主动地为其主子效劳,经常不断送来好米、好面、鸡、鸭、鱼、肉、蛋及香油等,因此困难时期,不但他家能常吃山珍海味、燕窝鱼翅、鸡鸭鱼肉、新鲜蔬菜、南北鲜果等稀有的珍贵食品,还经常让服务员给他的亲戚送去,就连妖婆张洁清的身影不离的大白猫,每天也必须吃三个富强粉的馒头,每月吃八斤富强粉,鸡鸭鱼肉更是同样有份。真是一人当官,九族沾光,猫狗升天。”“彭贼为了抬高自己,达到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他竟为宴请李宗仁准备了三个月。准备二、三次他都认为时机不好,最后等到各有关方面宴请完了,他才搞了家宴。”“金樽美酒千人血,彭贼称心狗颜开:这次家宴奢侈已极。席上有山珍海味、燕窝鱼翅、飞禽走兽、古巴牛蛙,博得了赴宴者的称赞,彭贼眉飞色舞,与李宗仁、张治中、程潜等,谈笑风生,解襟相吐。一顿饭吃了四个小时,彭贼还颇惋惜地说:‘不如在天津与贺龙一顿饭用了12小时多。’真是无耻至极。”“彭贼这次家宴搞得与慈禧太后相比,那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桌饭就够一个普通劳动人民五年的伙食费。彭贼拿人民的血汗挥霍,还企图和主席、总理比高低,处处想压倒毛主席。真是野心勃勃,十恶不赦。”见原北京市委机关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行政处六七一三工人联队及部分革命同志:《彭真的腐朽生活罪行》,1967年9月15日,已收入谭放、赵无眠编:《文革大字报精选》,第503-506页,香港明镜出版社,1996年版。)而革命者,如果说他们不得不吃饭,也一律是“野菜野果当干粮”。这使我想起自己童年时的笑话,每次看完电影,父亲都问我,是要做好人还是做坏人,每次我都毫不犹豫地回答:“做坏人!”原因是坏人可以吃香的喝辣的。食物是中性的,但是,在被意识形态化化之后,已经不再是食物本身,它不是用来充饥的物质,而是摆在革命者面前的一道考题,它关系到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刘思扬们看透了回锅肉的阴谋,因而,断然拒绝了胃部的请求。这是革命者的饥饿伦理。实际上,革命者的饥饿伦理,或者饥饿美学,是在一定情境下产生的,然而,它们却被绝对化,成为一种普适性的公式,它的最终目标就是排斥食物。这令我们想起孔夫子的名言:“割不正不食。”如果切割食物刀法不整,老人家将拒绝进食,他的精神洁癖达到了极致。“君子不食嗟来之食”,使得君子在满足胃的欲望之前,先要打听好食物的来路。充满节气的胃部将回绝一切来路不明的食物——更得况是对手的“恩赐”?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意识形态使一日三餐的合法性遭到否决。(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