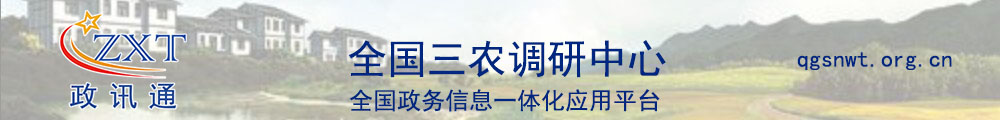怀念舅舅杨宪益:生活因你美好而难忘

赵蘅和舅舅一起过92岁生日

老来伴最后的日子 傅靖生摄于1999年
从此,不一样的生活
今天,11月最末一天,北方大部分地区的雾渐散,天开晴了。从早晨到天黑,人们各忙各的,微寒里一点清新一点尘埃。而我自己起床后照旧一件事接着一件事。电话很多,妈妈的,大姐的;媒体还没完没了,出乎我的意料。女友阿鸽从成都来,约我去美术馆见一面,而我需要去验汽车尾气,因为是最后一天期限……
然而我还是觉得生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在昨天——2009年11月29日,大家送别宪益舅舅之后。
29日前的那一周,即便老人躺在煤炭总医院冰冷的太平间里,我也会觉得他和我们还在一起,在这座他一向喜欢的、新旧面貌已大不同的都市里。他还依稀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他刚调到北京,印象“很清洁”,和平解放保留了完整的城郭。
23日到29日的一周里,我们大家睁眼时,舅舅闭着眼,我们睡了,做梦了,他也在“睡”。虽然他的梦我们无法知道,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安慰”!
可昨天,随着一束束鲜花和满地的花瓣在火焰中消失,一切全改变了……
从此我再不能像从前那样,可以在任何时候拨个电话,只要打声招呼:“舅舅,我今天去看你!”或是问他带几位慕名而来的朋友去拜访可不可以,然后我就可以立刻奔到小金丝胡同6号去叩那扇灰褐色斑驳的木门。舅舅也总是坐在客厅单只沙发上静静地候着,偏着头,用他那双黑黑细长的眼睛迎接我们:
“对不起,我不能站起来。”他做着欠身姿态抱歉地说。
从此也不再会有为舅舅过生日的大聚会了。以前的每一年,一到冬天,不管会漏掉谁,每次总归有很多人。好几年舅舅是和姨夫的生日凑在年底一起过。那天,我们几家做晚辈的,会散坐在老人家们身边,听他们谈天说地,讲那过去的故事。也常常是敏如姨妈主讲,舅舅笑眯眯听着,我妈不时插一两句话。但舅舅和姨妈对对子时,那简直是一堂古典文学课!
舅舅不如两个妹妹记性好,尤其是我姨妈,写清上百年的家谱,全仰仗她了。作为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三兄妹,依然共同坚持一个人要独立自强,无论男的还是女的,都要有所作为。难怪他们都不喜欢《红楼梦》,尽管舅舅的名气在老百姓当中主要来自这部中国古典名著,一听说翻译过《红楼梦》就了不得。他不会因为它有名就喜欢。但他说不喜欢并不等于不好,曹雪芹还是写得很好的。
舅舅姨妈和我妈妈他们仨在一起乐融融的画面再不会出现了!杨家到了他们这一代,本来只有他们仨还健在,如今他们仨只剩下两位老太太!
2008年12月27日,那是舅舅最后的生日聚会,这一天,他九十五岁。
我们大家族的擎天柱就这样坍塌了!
从此,在这座城市里,不再有舅舅杨宪益的身影了。尽管可能媒体会继续宣传报道下去,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甚至一百年,但他本人不会看到了。本来他就不在乎看到这些。
慈爱的舅舅
不能用三言两语说清舅舅对我一生的影响,更不可能在一篇文章里写尽我心中的舅舅。也许是一本书。那也难以表达一个长辈对一个孩子灵魂的荡涤。
先从儿时的记忆片断开始写点吧。
听我妈说抗战在重庆跑警报时,舅舅是牵着我姐姐的。大姐叫小苡,当时她只有三四岁,是外婆第一疼爱的外孙女。当时我妈正怀着我,她总是愿意跟着哥哥,挤在凄厉的警声下慌乱奔跑的人群里往城外的旷地疾走。那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情景!
从我记事起,从没见过舅舅和我们小孩厉声过。上世纪40年代末,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靠当助教的爸爸养活一家人。我们许多食品日用品都是舅舅支援的。舅舅对妹妹和我们几个小孩从来呵护备至。
我们常到南京舅舅家里玩,那里有一幢房和草坪。表哥杨烨蔫儿皮,我和表妹杨荧喜欢共撑一把伞,这些童趣还历历在目。幼年的我不会注意舅舅舅母和我爸妈谈话的内容,我不会懂得他们正面临着命运的抉择。妈说舅舅明确地说过,静如(我妈的娘家名)跟着我,带上小采(我的小名),我能养活她们。后来才了解,舅舅早就帮助地下党做迎接新中国的工作。去台湾的机票已由南京政府送来,但他留下来的心意已定。这也是我外婆的心愿。
1953年,高教部要派我的双亲去东德教书,没有带孩子一起走的政策,三个孩子怎么办?妈和舅舅商量。舅舅又说小采跟我们一起过类似的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总是要我。采访的记者也这么问过,我说我不知道,也许我乖吧。的确我小时候不吭不哈,只会闷头画画看书,这也符合舅舅家宁静的风格。这样的小孩是好带。
再后来,我真的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那年15岁。考试期间我和妈住在舅舅北新桥八宝坑胡同家里。考色彩那天,我因紧张把纸的反面当成了正面,结果画面洇了。我非常沮丧,在胡同里迷了路。后来派出所打电话叫大人去领我。我妈有点生我的气,舅舅赶紧说,找到就好,回来不要骂孩子啊。
考完试我回到南京等消息,心里忐忑不安。不久收到一份电报,是舅舅亲自填写发来的。从此我的命运和北京连在一起,我成了真正的“北漂族”!
在附中上学期间,每到周末,我就住在舅舅家。我学会了自己洗衣服,在澡盆里投净再晾到院子里。院子很大,有花木,四面是房,从这屋出门再进那间屋。关门声轻轻,说话声更轻。我也听惯了舅母打字的声音。她高耸的鼻梁,淡黄短短的卷发,瘦高俯身的侧影,会映在厢房带古色古香窗棂的玻璃上。那几年正是中国的饥荒年,听说舅母要求减薪。在他们家圆圆的饭桌上,出现了窝窝头。那也比我在学校里吃得好。一次,舅舅带我们几个孩子去东郊体育馆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休场时,他发给每个孩子两片面包,中间夹着黄油。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定是舅母的特供食品。当时我正处在发育期,那样的喷香解饿,一辈子也忘不了!
在舅舅面前,我们做晚辈的会永远放松。他是惟一的一位让我们不发怵的长辈。尽管他会失望。现在的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和他当年所追求并身体力行的,相差实在太远了!一次我们议论孩子爱看电视打斗动画片时,他说现在的年轻人缺少理想,不爱读书,这是我听过的惟一批评。舅舅对下一代、再下一代的情况,都看在眼里,嘴上不说,心里极有数。他的方式就是正面鼓励,能帮就帮,帮不了,也不干涉,让你有绝对的自主权。我有个画速写的习惯,他从来不干涉,我爱怎么画他都可以。
从来没有问过他为什么不喜欢《红楼梦》。但永远记得他在自传里说过他从小崇拜诸葛亮,因为那是有作为的人。
舅舅,我的导师
近十年,自己常发表东西,出了几本书,和舅舅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也多起来。这让我感到在舅舅的眼里,我已从一个孩子升等到可以和他平起平坐谈文学的阶段了。
因而,我会经常被他督促和询问,比如你下一本书是什么啊,你应该给你爸爸写本传。
特别是每逢出国归来,在我又给他看我带回的笔记和速写时,他就会肯定地说,这些可以出本书,完全可以出本书。我看来很难的事被他一点拨,仿佛已看到未来的曙光。我常常感叹,舅舅你太天才了,怎能理解我们笨的人做成事是多么不容易啊!
我难以忘怀的是,舅舅几次亲自帮我校对书稿。《拾回的欧洲画页》原文有30万字,厚厚一摞打印纸,压在他瘦瘦的膝上,他低着头要一口气看完。我守在一旁直紧张,怕他太累了,看完一节就打断他就劝他歇会儿,他总是说不累,没关系。
舅舅视力好得惊人。我曾给他配了副眼镜,他也不用。他一目十行,能很快挑出文章里的毛病,特别是英文的拼写错误。
书正式出版后我去看他。那天亲友不少,大家正聊着天,舅舅突然当着好多人的面问我:“小采,你以后是当画家呢,还是当作家?画嘛,像黄永玉能卖好多钱。”
我知道他又幽默起来了。但这突如其来的问话,让我张口结舌,脸一下子红了。
接着他为我未来的生计分析,让我又好笑又激动。
校对《下一班火车几点开》时,舅舅给我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说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会看懂过去的事情,可以在每一历史时期故事的前面,加上年号和说明,这让我豁然开朗。我照此办理了,果然让广大读者一目了然。2006年,当他听说我这本书在三联书店签名售书两次了,便马上表态:“要是我能走路,我也去。”我听了真是感动极了。
丁聪伯伯去世后,我很快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丁聪好大胆》一文,他既高兴又非常惊奇,他说这么快啊!我知道即使老朋友走了,他也希望他们被宣传,不会寂寞。
郁风阿姨去世前一天,舅舅还和我叨叨过她病重的消息,他表面平静,心里很惦记。他为郁风起外号叫“郁三刀”。他们都是对生死置之度外的豁达老人。我后来写了长长的悼文,他也看了。
今年8月,我去看他,当谈起自己这代人被耽误了的话题,我感叹地说,舅舅,我们比不了你们,外语、学问,都差得太远。
他静静地听着,然后显然是安慰我:“你已经很好了。”我一下子愣住,又要脸红了。这句话由舅舅嘴里说出来,现在还令我惶恐。
十年来,舅舅不仅给了我父辈的爱,还给了我导师般的恩情,恩重如山!
我总在想:爸爸走了,还有舅舅,舅舅走了,我还有谁?
那是一种和失去父亲一样的痛……
朴素的叙述方式来自坦荡做人
除了可以直接受到老人家的帮助,在舅舅和文学前辈那里,我才知道什么是朴素的语言。朴素才是最高的语言境界。还是舅舅住在友谊宾馆那会儿,一天我去看他。他应邀刚写完纪念钱钟书的文章。他递给我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舅舅的手稿。短短几页,我惊讶他写得这样直白,一点虚词儿也没有,真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不夸张不吹捧。但看得出来,他十分敬重和怀念这位当年的英伦同学、后来的老朋友。
我早就了解舅舅写东西,总是一遍完成,他从来不修改,不像我们许多人要斟字酌句地推敲半天。他的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便是只用很短时间一挥而就的。这本书充满他的杨氏独有的风格,洋洋洒洒,一气读下去,一点不累,片断里还会不时被主人公的各种奇怪的遭遇弄得忍俊不禁。读完,却会在内心升起敬佩怀念之意。
舅舅平时说话也同样简短而朴素,拒绝和接受都非常明确,又风趣又幽默,甚至小小的讽刺含在其中。有时候,你没有一定文化,不细细体味,还听不出来呢。
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只说一种话,真话。不趋炎附势,不说阿谀奉承的话,难怪他这一生遭遇种种不测依然坦坦荡荡呢!
他永远只会说:“欢迎!”
这些年,在舅舅家,除了偶尔碰上拄拐的苗子和郁风、嬉笑的黄宗江、认真的袁鹰等前辈之外,我还引荐了许多年轻的中外朋友给舅舅。久而久之,只要谁想去认一认老先生,就找我。我妈那边有时也遥控我,叫我带这个去,陪那个见。大家都爱戴我舅舅,无可厚非,只要老人家乐意。其中当然不乏有想沾点名人光的,也没什么,总比崇拜糟糕之人强。
每当我带他们过去,介绍完毕,我便坐远,候在一旁,那时我只是一个听者。
邵绡红去见舅舅那天,备了好多大白馒头。她一直致力写她父亲邵洵美,自然会聊这个话题。舅舅非说解放后他见过邵洵美和项美丽,绡红说不可能,因为她在上世纪40年代后再没回过上海。一个下午把我带入那个久远凄美的故事里。
《中国档案》的记者刘守华是第一次见老人。她一边听我舅舅说话,一边不停在小本子上记。舅舅完全不忌讳她是陌生人,和她说了很多老朋友的近况,谁摔了,谁住院了,甚至说最近又有一个老朋友走了,叫戴爱莲,我认识她很早,那时候她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
《人民日报》的年轻记者们一来,就毫不怯生地围拢在舅舅身旁,有的和老人聊天,有的举着高级专业相机噼里啪啦拍着。舅舅说你们可以到院子花园去看看。每到这时,我就领路前行,俨然一副主人姿态。我们从铁梯登上,四周一片四合院灰色瓦顶,远眺红灰相间的钟鼓楼,我说一到黄昏,邻家的鸽子飞回,先在你头顶上盘旋一阵再回窝。
请舅舅签名的不计其数。巴金的侄孙李斧几次淘来一大堆舅舅的旧著让老人签名,还要盖章。我总是哄他说,咱们今天就当做功课,练练手劲。舅舅笑眯眯一点不烦一一签完。
来客里还有帮助舅舅编书的,以前是雷音,有一阵李晶常去。后来的三年里,海归的范玮丽走进了这幢房子。她起先要写杨戴之恋,深入接触和交谈,她完全被老人的人格魅力折服了,以至于成了慰藉舅舅最末岁月的陪伴。送别式上英格兰民歌《Danny Boy》,是她献给老人的。
这些年里,舅舅还签了几本书合同,我没参与《漏船载酒忆当年》和再版的《银翘集》、《译余偶拾》,译林出版社的五种双语文库是我带编辑去的。还有今春,他亲自写下“去日苦多”四个字。这是他的最后一本散文集的书名,却没能写点自序,让我们有点遗憾。不过这很像满不在乎的舅舅风格。
多少书出版了,他很快也送光了。他从不自恋自己的作品,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每次来人,舅舅都会主动指指客厅外的那边:“你们要不要看我的房间,书柜里有你们喜欢的,还有石头,都可以拿。”这好像是他安排的又一个节目。大家被他催促着拘谨胆怯地走过去,小薛十分善解老人家意思,会立刻去打开柜门,让你随便挑。我自己往往会想到这些书来之不易,多么宝贵,越来越少,自然不大敢多拿。往往我象征性地选了几本回到他的身边,他就会问,这么少?假如你多拿了,他会很高兴地说声谢谢。
如果统计,舅舅“大撒把”的东西不计其数,比如香港中文大学赠送的文学荣誉博士服、杨宪益铜雕、贵州师范大学颁发的证书、大批珍贵古董藏书、自己译著和诗文集……甚至是出版书的稿费,有没有,他都无所谓。
五彩斑斓的石头是舅舅钟爱的亲自跑远路淘来的,如今已所剩无几了。
我知道舅舅并不富裕,一辈子翻译,只拿工资,没有什么稿费,他却慷慨地支援他的晚辈,只要他抽屉里有,只要他认为谁有困难。我大姐开饭馆一次失火,舅舅知道了,马上解囊相助一千美元。我头一次去巴黎,也是舅舅非要塞给我八千港币。去年他过生日,我特地买来全套《红楼梦》送去,结果他不但把书反送给我,还要附上书费。
一天有个外国女子来访,谈天中赞美了舅舅手上的戒指。舅舅听了,立刻脱下那只戒指,送给了对方。
舅舅淡泊名利的地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无法达到!
舅舅最大的遗憾
“爱国”一词这些年好像多起来。舅舅的爱国,不是大话,不是假话,不是非得要贬低他国抬高自己。他的爱国心与生俱来,从很小就开始了。上中学时作为富家子弟却带头抵制日货,担任牛津中国留学生主席期间,他号召抗日简直叱咤风云。1940年,中国陷入战火离乱当中,他谢绝了哈佛和牛津大学的聘请,执意回国。当时他的英国未婚妻戴乃迭才刚20岁,问他干嘛要这样做,他回答:“中国人嘛。”
做自己不会后悔的事,不做不能原谅自己的事。这就是舅舅的信条。
许多人好奇地想听舅舅当年坐牢的事。舅舅从不回避,对那些现在听来令人窒息恐怖的细节,舅舅总是说得轻描淡写。一次次重复那段不堪回首的荒唐经历,对一位老人,是并不愉快的。但舅舅不但敢于直面,还说得很平静,很幽默,好像这种事发生在别人身上似的。
山东电视台来采访拍摄《数风流人物》,年轻的女记者问他人生体会,他直率地说,虽然共产党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但是现在不做了,我对国家还是比较满意。
接着记者问:“杨老,那你觉得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舅舅立刻回答,一语惊人,他这样说:“本来我们说好白头一块死,结果她先死了。”都说舅舅舅母相爱,但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直截了当的表白。第一次亲耳听到,心里一颤,顿时感到古今中外,所有的爱情,都会在他们的旷世之爱面前黯然失色!
与死神争夺舅舅
舅舅刚离世九天,与死神争夺舅舅那惊心动魄的一天天还历历在目!
11月8日,我大姐赵苡专程从南京来看他,半年多不见舅舅,见他衰弱成这个样子,心软的大姐一下子就哭了。但这时的老人已经完全喑哑了,还认得这个大外甥女,是否还记得当年牵她的小手跑警报的事呢?
大姐的到来也大大缓解了我连日跑医院的辛苦。一周后,她身心交瘁差点病倒。
我妈在电话里说,她为她的两个女儿骄傲,我想说,我为我善良的大姐感到骄傲!
大姐曾因舅舅坐牢的事,受过株连,多年挣扎在底层,非常痛苦。今天老人去了,一切灾难化为乌有。
我只感到有股力量,助我快快振奋起来,我懂,那是敬爱的舅舅赐予的!
写于2009年12月2日,宪益舅舅仙逝第九天。(文/赵蘅)
杨宪益生平简介
杨宪益,中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1914年1月生于天津。他在中国语言文化和西方语言文化方面具有深厚造诣,曾将许多优秀的西方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他与英籍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了包括《离骚》、《史记选》、《红楼梦》、《鲁迅选集》等上百种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其中,《红楼梦》三卷本全文英译工作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历经坎坷,在70年代完成并陆续出版,引起中外文化界和学界轰动,成为最受中外学者和读者认可和推崇的经典译作,为中国文学和文化赢得了更加广泛的国际影响。2009年,杨宪益以其在文化翻译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杰出贡献,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09年11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